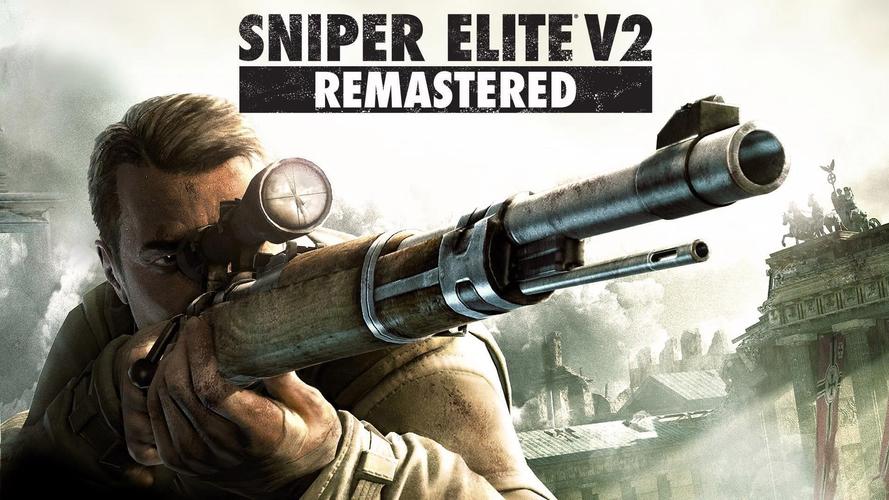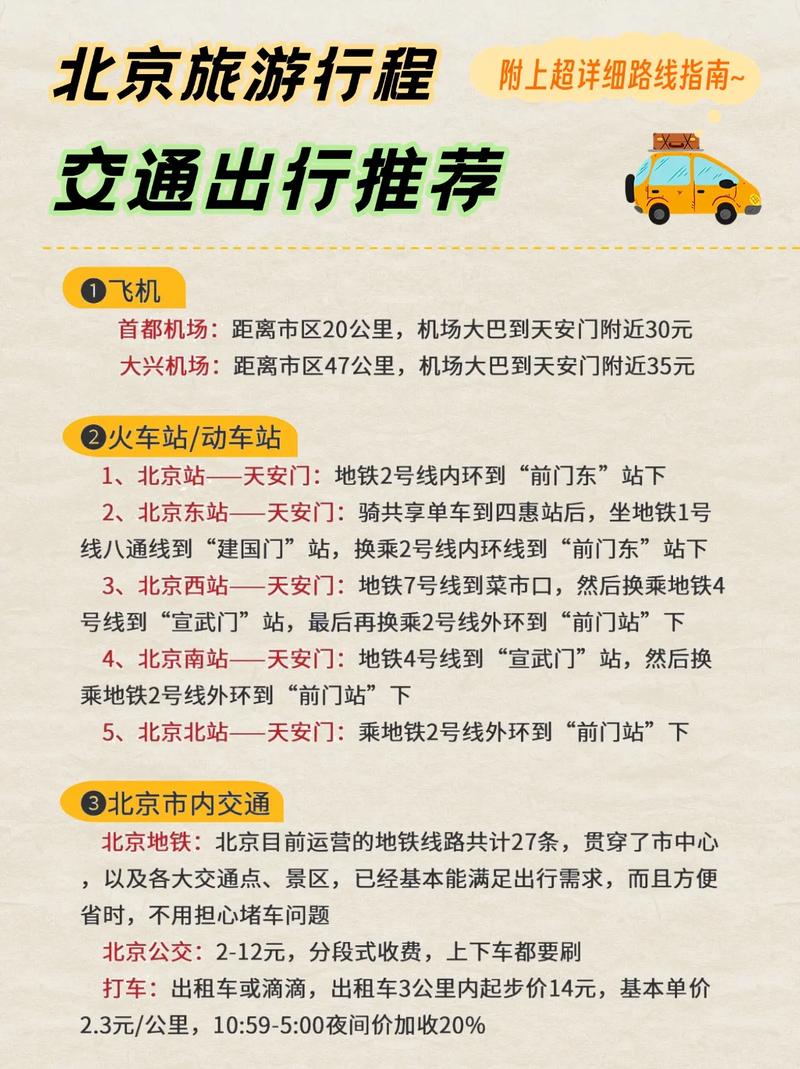那天刷手机看到幅古画,角落盖着红艳艳的印章,脑子里突然冒出个问号:古人写字画画难道只用黑墨?这事儿勾得我手痒,非弄个明白不可。
一、翻书翻到眼发酸
先是把书房里堆的十几本讲文房四宝的书全扒拉出来,摊得满桌满地都是。蹲在书堆里翻了俩钟头,眼都看花了,终于在一本讲制墨的老书里揪出句话:“古墨非独玄色,亦有朱、紫、青、黄诸品。”
重点来了!- 明朝《墨谱》写着道士画符用朱砂墨
- 宋朝笔记提过青楼女子用紫墨写情诗
- 最绝是清朝内务府档案记着皇上批奏折的黄墨
二、动手复刻翻车现场
第二天直接杀到化工市场,买了包天然朱砂粉。老板斜眼问我:“小伙子玩篆刻?”我嗯嗯糊弄过去,攥着塑料袋溜回家。
按古方倒了半碗骨胶加水熬,厨房瞬间弥漫着一股子炖蹄髈的味儿。等胶水咕嘟冒泡了,赶紧把朱砂粉倒进去搅和。这红粉子特别不听话,沾水就结块,抄起打蛋器猛搅还是疙疙瘩瘩的。

眼看灶上煮的“红汤”快烧干底了,手忙脚乱关火倒进月饼模具里。没承想胶水冷得太快,模具里的半凝固墨团死活磕不出来,拿菜刀撬了半天,愣是撬出个歪嘴葫芦造型。
三、血泪测试日记
等墨阴干这礼拜可急死我了。第七天大清早,抄起自制“朱砂葫芦”在砚台上猛磨。好家伙!磨出来的红色墨汁跟番茄酱似的浓稠,毛笔刚蘸上就滴答得到处红点子。
不死心又加茶水稀释,这下可写在宣纸上像掺了水的血痕,写两个字得蘸三次墨。试写《心经》才抄三行,整张纸已经被红色墨渍泡得像凶案现场。
这时候才恍然大悟:
- 彩色矿物粉比松烟沉得多
- 植物胶根本挂不住色料
- 写十个字得磨半时辰墨
四、茅厕里想通大道理
蹲马桶时盯着卫生间红瓷砖发呆,突然拍大腿:难怪古画里彩色都是拿来做标记!皇帝能用黄墨批“知道了”,是因为奏折上就写三个字;道士画符用朱砂,符咒也就巴掌大。
后来查证果然如此:宋代《营造法式》写营造文书用五色彩墨标注建筑尺寸,每支颜色顶多写七八个字;明代府衙的田契用不同颜色区分类别,但正文全老老实实用黑墨。
说到底,不是古人不想用彩墨写情书,是技术不允许!彩色墨颗粒大、掉渣、难保存,写着写着纸先烂了。人家黑墨是松树烧的烟灰拌牛皮胶,写出来的字能千年不褪色。我那坨朱砂墨才晾三天,边缘已经裂得像干涸的河床。
这趟折腾完,书房地板上永远留着几块洗不掉的红点子。每次拖地看见它们,就想起那些在历史里褪了色的紫情书、黄圣旨、红符咒——五彩斑斓的文明,终究还是被黑色墨迹传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