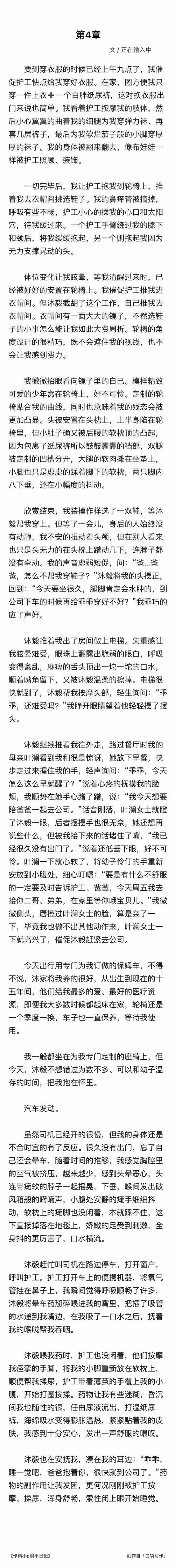翻箱倒柜挖老黄历
那天整理书架,灰呛得我直咳嗽。一本硬壳毕业纪念册砸脚上了,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揉着脚指头翻开册子,黑压压一片小脑袋,中间杵着几位老师,脸都笑皱了。脑袋里就崩出那句老话:“桃李满天下”——这桃李的,到底指谁?是说老师学生遍地?还是夸老师教得我自个儿上学那会儿,老师点名我都能溜号,现在倒琢磨这个,臊得慌!
越想越憋不住,蹬上拖鞋就去翻书房角落那个积灰的饼干铁罐子。掀开盖儿,一股陈年纸张味儿。里头全是过节塞给老师的破贺卡,纸都发黄了。蹲地上挨个扒拉,还真扒拉出点东西来。
第一个故事:牛皮纸里的毛票子
抽出来一张褪了色的明信片,正面印着特丑的大红花。翻过来,背面是我初中那会儿狗爬的字:“张老师节快”。盯着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,手都开始抖。
那年家里交不起学杂费,快开学了,我妈急得嘴角起燎泡。我硬着头皮去办公室找张老师,蚊子哼哼似的说要缓几天。这老太太,教数学的,平时板着脸,粉笔头扔得贼准。那天她一声没吭,拉开抽屉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,抽出一小沓钱塞我手里。“拿着,赶紧交去!” 那钱,十块五块的都有,捏得发皱,油乎乎的。我一低头,眼泪直接砸信封上了,糊得那牛皮纸上一滩水渍。那会儿就觉得,讲台上那个扔粉笔头的老太太,真像把伞。

第二个故事:被踢倒的板凳
又从罐底抠出一张硬邦邦的贺卡,喷着廉价的闪粉。一抖落,闪粉掉一裤子。这是高二教师节凑份子买的,署名是“全班同学”,就班长瞎写的。我撇撇嘴,想起我们那物理王老头。
王老头个子矮,嗓门大,脾气暴。我高一物理烂成一锅粥,试卷满江红。有次他上课讲卷子,走到我旁边,瞅了眼我摊开的卷子,上面红叉叉触目惊心。他“咣”一脚,把我凳子腿给踹歪了!我懵了,全班鸦雀无声。“就你这样,物理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!” 他那嗓门震得我耳膜嗡嗡响,脸烧得能摊鸡蛋。下课后他叫我留堂,我抱着被踢歪的凳子,腿肚子直哆嗦。他也没多说从讲台下扯出几本习题册拍我桌上:“每晚放学到办公室找我,老子给你回炉!” 就那破板凳,硬是陪我熬了小半年,办公室灯天天亮到看门大爷催。后来高考物理真没拖后腿,查分那天我在家嗷了一嗓子,隔壁狗都跟着叫。
第三个故事:被红笔叉掉的毕业设计
摸出一张贼薄的打印纸,A4大小的,是我本科毕业设计初稿的废纸,反面被我当贺卡用了。正面影影绰绰能看到导师李教授的批注,一堆大红叉叉刺得人眼疼。
李教授那会儿在我们系里以严谨出名,眼神跟探照灯似的能把你论文烧出个洞来。我这论文写了俩月,胆战心惊发他邮箱。第二天一大早,邮箱弹出回复:“整体方向错误,建议重写或换题。” 附件里我的论文密密麻麻全是他批的红字和问号,天灵盖都要凉透了!我瘫在电脑前半天没缓过劲儿。下午硬着头皮去他办公室,推门就见烟味缭绕,他泡着浓茶翻我那堆垃圾。“哭丧着脸没用,来!划重点,哪些不明白?” 他从头到尾一条条抠,茶都凉了重泡了两回。熬了三个通宵改完,熬得我眼前飞蚊子。新的一稿发过去,他回得更快:“下午四点带上U盘过来。”过去一看,他在那稿子里又画了新的叉叉圈圈——但这回是具体细节上的修改,方向对了!临出办公室门,他捏着烟屁股吸了一口,说:“总算像个样子了。记住,你做我的学生,第一课就得学会把‘重写’这盆冷水,泼自己头上。”
拖出个烂木箱的收获
一屁股坐回地板上,腿上堆满了老贺卡烂纸片。屋里灰蒙蒙的光线里,那几个老师的面孔特别清晰地晃悠:张老师递钱时手上的老人斑,王老头踢板凳爆的青筋,李教授熬夜抠我论文熏黄的手指头……什么桃李满天下,根本不是什么文绉绉的形容。
这三个“神奇”老师的神奇之处, 我算是咂摸出点味儿了:
- 张老师塞钱那信封里的“油乎乎”,比一万句鼓励都暖
- 王老头那“爆裂一脚”,踹醒装睡的我
- 李教授“重写”俩字一扔,逼我学会“自个儿泼冷水”
这哪是种桃种李的园丁?这帮人,分明是在我们这歪脖子小树上,又锯又砍又嫁接。痛是真痛,死倒也没死成,硬是让我们硬邦邦地挺直了点儿。桃李满天下?我看是——老师这行当,专治“不开窍”的花苞,管它蔫了还是炸了,憋着一股劲儿也要给你憋开花! 我那饼干罐子合上了,盖子扣得咔哒一声响。